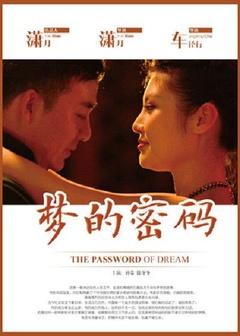
梦的密码微电影
- 主演:
- 徐冬冬,孙荣
- 备注:
- DVD版
- 类型:
- 微电影 剧情,奇幻
- 导演:
- 潇月
- 年代:
- 2013
- 地区:
- 中国
- 语言:
- 国语
- 更新:
- 2015-09-20 22:14
- 简介:
- 《梦想密码》讲述了现代人在工作、生活、情感的三重压力下寻找梦想的故事。这部电影讲述了现实、回忆和......详细
相关微电影
梦的密码微电影剧情简介
微电影《梦的密码微电影》由徐冬冬,孙荣 主演,2013年中国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梦想密码》讲述了现代人在工作、生活、情感的三重压力下寻找梦想的故事。这部电影讲述了现实、回忆和...
《梦想密码》讲述了现代人在工作、生活、情感的三重压力下寻找梦想的故事。这部电影讲述了现实、回忆和...
梦的密码微电影相关影评
@豆瓣短评
《梦》是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在80岁高龄时拍摄的影片。它是大师晚年对电影表达新方式的一次大胆探索。影片由八个零碎的梦境组成,每个梦境时长十多分钟。表面上看来,八个故事各自陈述,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然而在表达主题和情绪营造上却彼此呼应。大师籍由这些小故事,对人类进行深刻的反思。
第一个梦:小朋友在一个阳雨天里头不听妈妈的告诫,偷窥了狐狸的婚礼,触怒了狐狸。狐狸留下一把匕首给妈妈,让她转交给小孩并要求他以死谢罪。妈妈把小孩赶出家门,叫他到狐狸的居所请求原谅。
第二个梦:女童节里,男孩在“第六个女孩”的引导下闯入桃园,与桃树的灵魂对话。桃魂要求他留在这桃园,为砍尽桃树的家人受罚。后来却发现男孩与家人不同,他是热爱桃花的。于是这些桃树的灵魂就为他带来最后一片怒放的桃花。
第三个梦:几个登山队员在赶往营地的途中遇上暴风雪,虽然营地就在附近,然而他们对自己、对队友的怀疑让他们在绝望中几乎全部毙命。就在最后一个队员弥留之际,他用坚强的意志力抵挡住了死神的诱惑,终于带领队员在阳光的指引下到达营地。
第四个梦:军官走过长长的隧道,在隧道的另一边看见死去的部下。
第五个梦:年轻人走进梵高画的世界内,拜访凡高。
第六个梦:核电厂爆炸了,有毒的放射物质把万物赶绝,把大地变成一片废墟。一个科学家、一个青年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被逼到海边,科学家跳崖,剩下青年妇女在做无力的反抗。
第七个梦:在一片死寂的废墟里,青年遇到了“食人魔”。得知这个世界受到辐射的影响,已经畸形。人类变成食人魔,弱肉强食并被头上生出的角折磨着。
第八个梦:青年来到一片世外桃源。这里的人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平静安稳。青年见证了这里的一场“快乐的葬礼”。
电影的多个段落都采用舞台化的造型和环境。短短的十几分钟内,虽然只有寥寥几人的对话活动,但人物的身份安排本来就具有代表性。巨大的矛盾与冲突被浓缩在零散的小故事当中,种种元素造成的张力表达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深刻的意旨。
第一个梦里,小男孩对狐狸的窥探行为是一种人类猎奇本能驱动下的僭越。男孩代表人类的阵营而狐狸所捍卫的是自然界的秩序。母亲的角色充当公正的裁判。男孩的探险发生在丛林,茂密的树丛、斑驳的阳光和晶莹的雨水把大自然的清爽透亮表现了出来。也为狐狸的出现提供一个神秘并充满灵气的舞台。在景别方面采用大全景。构图方面,近景是壮实高大的树木,密林中行走的小孩仅占很小的比例。男孩的稚嫩弱小和大自然的伟岸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白雾中若隐若现的神塔和传统戏剧的配乐“仙化”了丛林(日本传统戏剧大多起源于祭祀活动,表达一种对神灵的敬畏),为狐狸的出现进一步营造气氛。雾中的狐狸造型不但舞台化,还很有日本传统戏剧的特色,从造型到舞步都规整考究,在刻画狐狸“神灵”身份的同时强化了“秩序”这一概念。同时也影射了躲在大树后的小孩对秩序的破坏。破坏秩序的小孩受到的第一重惩罚是失去了“家”,紧闭的家门隔离了他与过往单纯宁静的生活。第二重惩罚是“以死谢罪”。故事的最后是男孩拿着匕首,在一片山花灿漫中走向彩虹(狐狸的居所)。在这里,彩虹的作用只是再一度神化狐狸这一大自然的“神灵”,并不代表狐狸已经原谅了小孩。遍地的鲜花与前方灰暗的山景形成色调上的强烈对比,预示一个并不明朗的未来。人类应该负起责任来,为自己鲁莽的行为赎罪。
第二个梦里,随着小男孩的移动,一树桃花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桃红的柔光。周围暗沉的色调和门框都对桃花起到了强调作用,使她显得特别的圣洁,特别的美。随后小男孩进入房间,鲜红的布匹以明亮强烈的色调引起了小男孩和观众的注意(当然小男孩注意它的目的同样是引起观众注意)。陈列在红布上的女童节人偶精致华丽。它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今天是女童节(日本的女童节人偶平时都是收藏起来的)。几个人偶的镜头越切越近,灯光把它们打得晶莹剔透,神情栩栩如生,仿佛要活过来一般,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给桃园里的“桃魂”一个静物的参照,以至于观众看到后来的“桃魂”时就会想起它们并产生对照。在男孩观看人偶的过程中,传统戏剧的配乐响起。它与随后“桃魂”起舞的那一段音乐相同。影片借助这两方面的讯息暗示观众,男孩在桃园里看到的“桃魂”实际上就是女童节的人偶。在日本,女童节人偶是有灵魂的神圣祭祀物。而影片在这里把人偶和桃树的灵魂画上了等号,一方面增添童话色彩,一方面把桃树神化,同时也把没有感情的树木人格化。于是自然生态的代表“桃魂”与人类的代表男孩开始了冲突两方的对话。对话过程中,男孩在地势上处于最低处,所以镜头经常要采用俯拍,而“桃魂”的地位显然是高高在上的。他们(尤其是王)拥有裁定的权力。他们声音空灵、服饰高贵,代表着自然一方的神圣力量。然而被他们所质问的小男孩显然没有丧失热爱自然的本性。“桃子可以用钱买,但是要上哪儿去买一片开满桃花的果园呢?”孩子问“桃魂”。这时采用的是“桃魂”的主观镜头,通过这样一个换位,孩子面对着镜头向观众、向人类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一场桃花瓣的雨下得满满的,那一枝枝怒放的桃花占满了整个屏幕。紧接着一个个突兀的桃树干把男孩的美梦打碎,也用强烈的视觉反差震碎观众的心。到这里,动人的旋律陡然降了八调,周围一片静默。怅然的音乐响起,男孩四顾,独剩一树桃花在风中摇曳。
第一个梦和第二个梦同样运用了日本传统的戏剧风格来体现大自然的神秘神圣。所不同的是,第一个梦关于惩罚,第二个梦关于奖赏。第一个梦体现的是自然神秘严酷的一面,而第二个梦却是它亲和美丽的一面。所以在音乐上,第一个梦相对诡异阴森,第二个梦却有一种祭祀或盛会的味道。从服饰上来说,狐狸的服装采用冷色调(即使是婚礼),而“桃魂”的服饰采用的是暖色调。两个梦都是关于孩子的,它表现的是一个小朋友的梦。因此无论是布景、光色还是剧情设计都充满了朦胧奇幻的味道。
一片风的怒吼声把观众带入第三个梦。画面灰蓝,能见度很低,几个登山队员步履蹒跚走在一片冰雪覆盖的世界里。呼吸声、脚步声和其他动作的声音都被不同程度地放大。后景发生雪崩,前景尖而长的冰从上方垂下,厚厚的雪一直积到人的大腿。而人的身上也铺着一层白雪。整整六分钟内没有一句对白。画面和音效都在单调中强调着这恶劣的处境。这样的开场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种疲惫、严寒、险恶和艰辛。观众在感觉上度过的时间不会仅有六分钟。登山队员同样感觉到时间的延长效果。意识模糊的队员说出第一句台词:“天又黑了。”这无疑更添绝望。在绝望中,队员们开始怀疑:怀疑方向,怀疑时间,并且失去了坚持的毅力。只有走在最前方的那一位,他坚持时间没错,方向没错。“我们的营地就在不远的地方。”他是最清醒的一位,也说明他是意志力最坚强的一位。这为他随后摆脱死神诱惑提供个性基础。一个又一个队友倒下了。死神伪装成温柔的美人,对他进行催眠:“雪是温的,冰是烫的。”让人舒心的安魂曲飘荡,队员在轻抚中几乎睡去。而睡去意味着死亡。当他用最后的意志企图起身时,突然一阵暴风雪的斯吼打破了宁静的歌声。在声效上,现实与幻象产生对比,体现队员在意识上的自我斗争。虽然神情依然温婉,死神按在队员脖子上的手却近似于掐喉。她头发在风中飞舞,在队员的反抗中,她终于恢复了狰狞的面目,随风飞走。这是一个关于意志力的梦。抵抗的级别逐渐升高。首先是恶劣的环境。这是可以看见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大家都调动起浑身的意志力对它进行抵抗。但诱惑是无形的,那美丽的面孔,那温柔的微笑都与死神的概念相去甚远。所以队友们说完“有人来”就倒下了。诱惑是对意志力的最大考验。甚至会有观众看完故事还不知道那位美人的真实身份,甚至有人即使知道那是死神的诱惑都选择安详地睡去。这就是诱惑的恐怖。大师所描绘的诱惑不但考验了登山队员也考验了观影的人们。既然迷幻让人沉醉,又有多少人愿意选择清醒?然而赶走死神之后,暴风骤停,画面变得清晰,阳光再次出现,美丽的风光只留给坚持到最后的人。队员在胜利的号声中举目四顾,看见巍峨的群峰被冰雪覆盖,雪花在峰顶飞舞。很明显,这些空镜头要么调用资料要么外出取景,然后利用蒙太奇的链接效果使他们产生关联,使得成功的喜悦通过一片美景在摄影棚中被放大。当然,摄影棚内的色调光线都要小心配合这些美景。美景神情交替切换,渲染成功的欣喜。营地被太阳照得发亮,夸张地设置在几步之遥。意图表达“紧要关头不放弃,绝望就会变成希望”。
第四个梦,男人的服装表明他军人的身份。镜头跟随着军人,背景从一派自然风光转向幽深隧道。军人主观镜头,黑色的隧道越来越近。黑色代表死亡、悲哀和压抑,而隧道隐含着对时空、生死的跨越。军人走向阴阳的交界。一只恶狗从隧道跑出,对着军人狂吠。腥红的灯光打在它身上,使它看上去更加狰狞恐怖,仿佛是从地狱闯出来的恶灵。长长的幽暗隧道,与回音重叠的脚步声,制造出一种恐怖、阴森的气氛,让人不安。当军人走出隧道时,象征死亡的夜幕已然降临。隧道中走出了一位牺牲的战士。战士的造型非常舞台化:暗红的血迹深深地渗透在破烂的军装里,皮肤泛白透着蓝灰色,脸部通过夸张的化妆效果描绘出骷髅头的模样。那是一副恐怖的死人的造型。就这样,战争中的惨死者和生还者被放到了一个画框内进行对话。战士的第一句话就很自然地交代了主角的身份:“指挥官。我真的殉职了吗?”对生存的愿望,对家人的眷恋使得这位士兵不能相信自己已然惨死。一步步的进逼,一个个的疑问,指挥官哑口无言只能一步步后退,被逼到墙边。画面中士兵处于左上角而军官处于右下角,两个极端的位置配合两个极端的身份,张力拉得很大。战士指着远处群山当中的一点灯光,转过头来,悲伤地说:“爸爸和妈妈还在等我回家。”这个画面相当漂亮。远处的群山在夜色中都已灰暗,只有山中那一点白光色调如此明亮,为战士的归途指明方向。但再明亮它也终究是一点而已,那么伶仃,那么微弱。就像一捏就灭的希望。近处战士在遥望,远处亲人在等待,但他们已经阴阳相隔,永远走不近彼此。这就是画面的感染力,也是大师级的功力。如果镜头只是对着战士,哪怕再大的特写,再凄凉的表情都不足以表现这一种绝望。这样的绝望是战争带来的。它夺取的不但是生命,还有希望、和平与爱。无伦是死是生,都得饱受它的折磨。第三小队整齐站在隧道口,队长报告:“无人伤亡。”根据之前的观影经验,观众可以从造型上辨别,他们其实已经全体阵亡。视觉与听觉造成的极端反差造成生与死,荣誉与屈辱的强烈对比。指挥官的自责以及对战争的恐怖回忆被形象化为一只狗,从隧道的入口尾随到出口,从生尾随到死。战争的可怕回忆将会伴随着他度过一生。那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创伤。在这个故事里,通过死生者的对话,黑泽明把战争的罪恶狠狠地披露。那是在利益与征服欲的诱惑下,显露人类劣根性的愚蠢行为。
告别了风雪肆虐,告别了死亡隧道,镜头展现油彩描绘的凡高。青年入镜。镜头跟随着他展示一幅幅凡高的作品。青年拿起行囊,戴上帽子,走入凡高画的世界里。镜头通过这些动作隐喻:是凡高让这位青年走向油画的世界,走向创作的世界。随着西方古典旋律响起,凡高名作《吊桥上的马车》在洗衣声和谈话声中活起来了。青年向画中的洗衣妇人问路,洗衣妇人语带讥讽:“小心,他住过疯人院。”一句轻描淡写的嘲笑道出了凡高的困窘:就连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不朽形象也笑他是个疯子。可见当时的他与世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凡高的画作没有对基督的颂赞,没有对圣经故事的复现,没有对贵族的谄媚,他终其一生在歌颂太阳歌颂自然。他的画作没有达芬奇与伦勃朗的细致逼真,他表现的是彭湃的激情、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光明的向往。黑泽明早年热衷于绘画,成为画家可能是他终生未能实现的梦。但他有着和凡高一样的艺术激情与执着。他们同样尝到过不被世人理解的辛酸。“黑泽明之于电影,的确就像他自己塑造的武士一样,有殉道者的执著,甚至带点儿疯狂的意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和斯皮尔伯格,和科波拉,也和伊斯特伍德不同。在好莱坞的这些大人物看来,电影最多只是一种生命中的价值,而对黑泽明来说,电影就是生命本身。黑泽明曾经躲在卫生间里割腕自杀,原因就在于不能拍电影导致精神崩溃。”黑泽明说:“我,减去电影,等于零。”这种疯狂与执着籍由他眼中的凡高反映出来。一身染满油彩的凡高看见青年手拿画板,第一句话就是:“Why aren’t you painting?”——你不需要站在后面战战兢兢对我顶礼膜拜,如果你热爱画画,你必须拿起笔来。而你该崇拜的不是我,而是伟大的自然。大师利用一组隐喻蒙太奇把凡高作画的镜头和火车行驶的镜头交互切换,表现出他那种作画的激情和冲劲。黑泽明特别选择凡高失去耳朵之后去“拜访”他。针对世人对他切耳行为的疑惑,电影里的凡高解释说:“我画不好自己的耳朵,所以把它们切了。” 且勿论这是否凡高切耳的本意,但这就是黑泽明眼中的凡高。于他而言,“凡高,减去绘画,等于零。”他在借凡高表达着自己以及自己终生追求的境界,当然也顺带借凡高赞颂美丽的自然风光。凡高走后,青年在火车的鸣笛声中奔跑了起来。之前的一组蒙太奇把火车与凡高的创作激情相捆绑,所以在这里,本不该出现在麦田里的鸣笛声变成了一个符号,它标志着凡高精神对青年的鞭策。随后青年籍由特效带领观众行走在凡高的画作里,黑白的景物映衬出一个硕大的红太阳。那是凡高的标志。画作按照青年的身高比例被放大,甚至观众可以看到坑坑洼洼的油彩。利用这种特效,黑泽明给观众一个机会,通过凡高的画作,深入、细致地去感受他的内心世界。故事以凡高最后的名作《麦田里的乌鸦》收尾,从虚幻回到现实,与开头呼应。那些乌鸦代表艺术家孤苦寂寥的内心深渊,黑泽明有意夸大乌鸦数目,他所宣泄的是同样的悲怆。与开头青年戴上帽子的动作呼应,青年凝视《麦田里的乌鸦》,脱下了帽子。他代表黑泽明本人,向凡高致以崇高的敬礼。
色调从清晰明朗转向模糊灰暗,第六个梦的开头一片恐慌。雄伟的富士山在一片火海中仿佛震怒的天神。人类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山下四串逃命。逆流行走的主角被突出。大师非凡的构图再次产生隐喻和对比:富士山所代表的自然阵营与人类之间力量悬殊。在美丽的富士山被激怒后,日本变成炼狱,渺小的人类无力反抗,只能逃命。悬崖边满地垃圾一片废墟。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开始充当“说书人”的角色,告诉观众发生什么事。本来没有颜色的各种毒素不但被“染上”了颜色,还如同瘴气般飘浮在空气中。影片通过这种手法把威胁形象化,使得冲突更加明显。也很直白地表明,这片土地人类无法再踏足。一番对话引出穿西装者的身份——“对不起,我就是那些罪该万死的人之一。”这句话一道出,几个人即刻归类到了不同的阵营里,他们不再是单纯的逃难者。男人、妇女和儿童,这三类受害者一类比一类无辜,一类比一类脆弱。他们和肇事者站在一起,一方疯狂地质问诟骂,一方愧疚地看着惨状听着怨愤。肇事者身着西装,分明暴露核工业给他带来的利益与地位。然而妇女却牵着两个未懂事的孩童,背着一个婴儿。一方面刻画出她伟大的母性,从而与残忍的灭绝摧残产生对比,一方面强调他们的可怜无辜。一个大爆炸把中年男人充满悔恨愧疚的脸照亮,然后他跳下悬崖。在享有金钱与地位之后,懊悔与灭亡尾随而来,这就是肇事者的结局。辐射扩散到悬崖边,男子在红烟的包围中拼命抵抗。生存的渴望变成男子拼死的挣扎,在布满屏幕的红烟之中显得无力。象征灭绝的红烟愈加稠密,让人绝望,让人窒息。这一个梦表达了黑泽明先生对核问题的忧虑。
一片死灰的大地,阳光透过密布的浓云投向一片废墟。青年行走了近四分钟,跨过山头,走过瘴雾,还是一片灰的死寂。与第四个梦的开头异曲同工,黑泽明有意把这些简单的画面讯息反复交代了四分钟之久,旨在观影感受上传递给观众一种没有生命痕迹的荒芜。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影出现在雾中,在造型、环境和姿势的强调下显得诡异狰狞。他头上的白角虽小,却由于它本身颜色的高调突兀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在日本,这是食人魔的造型。因而在日本人看来,这个造型会更加恐怖也更有寓意:人类的自大自私把自己变成了吞食自己的怪物。另外,在环境塑造上,就连美的代名词——花朵,也变成了这副模样。以畸形的植物衬托畸形的人,人类僭越本分破坏自然和谐,造就了这么一个不堪入目的世界与自己。人类被辐射成食人魔的模样,过着人吃人的生活。即使在文化灭绝,濒临绝种的关头,阶级依然存在:角多者欺压吞食角少者。在这里,食人魔不但是说书人和引导者,更对人类破坏生存环境的愚行进行犀利指责。腥红的水塘边,许多“食人魔”痛苦地嘶叫。这地狱的景象在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告诉世人,破坏生态这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什么景象。起到很好的告诫作用。这个梦一方面是再度以辐射和环保为题材,另一方面也把人类最丑恶的灵魂暴露。
在述说了七个梦境以后,大师用来结尾的第八个梦,有关于死亡礼赞。同时也把他的理想国展现在世人面前。那里没有锋利的匕首,没有突兀的树桩,没有肆虐的风雪,没有狂吠的恶狗,没有爆炸的核电站,没有死寂的荒芜。美丽的大自然展现在观众面前,穿越过浓烟与废墟之后,画面里水车转动,流水潺潺,一切安宁祥和。平淡的乡间景色忽然显得如此珍贵。这样的景致无疑与第七个梦的结尾处产生极大的对比。一天一地的生存状态使得观众很直观地做出本能的选择趋向。在青年与老者的对话中,老者语调平淡却句句指向人类的愚昧。通过他俩的问答,“水车村”的观念与现代社会的观念产生对比碰撞。老者说出的正是黑泽明本人的心声:一种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生存法则。在说话过程中不断穿插美丽的风光和青年的表情,在镜头语言上增加老者言语的说服力。故事开始时,一群孩童排着队伍,采花放到一个块石头上。无论是小孩的行动还是青年的视线都将焦点引向那块石头。石头的地势较高,摆放在画框的中心位置,青年离开后,镜头为它停留好一阵。这些强调都使观众产生好奇,对它留下印象。后来利用这个伏笔,故事很自然地引入死亡礼赞的主题。原来那是一个浪人的坟墓。浪人一生漂泊,孤苦无依,客死他乡。然而水车村里的人们却给他一个美好的归属。死亡于他而言反而变成了一种解脱,一个安乐的归属。这时画外传来若隐若现的庆典乐声,通过老者的一番解说,很自然地把死亡庆典渐渐带入。“年纪大了,自然就会死的。” 人生在世做出贡献,死后理应得到尊敬。这是达观,是顺应自然。阳光透过树荫投下斑驳的光影,村民抬着遗体一路载歌载舞。在经历了七个故事的坎坷征途后,那是一个安详的歇息,是一个句点,是极乐。也是黑泽明所向往的最终归属。
这部影片具有很强的实验性质。在两个小时的观影时间内,黑泽明向观众展示内容上毫无关联的八个小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主题都很深刻。在短短的十来分钟里如何把主题突显,起到预期的教化作用,这个问题很考功力。大师极力调动起环境、造型、动作、构图和声效等电影技巧,让它们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叙事。人物极具代表性,台词不但一针见血,还不时会有大段的说教,甚至会代表黑泽明本人,直白露骨地把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这对传统艺术(尤其在中国)所讲求的留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画面上,有说黑泽明与主流创作者不同,追求的反而是平面化的构图。在电影里,有些背景的构图已经表现化到与舞台背景靠拢的地步(在第6、7个梦里尤为明显)。到底这样的效果好是不好就见仁见智,但是大师在80岁高龄还勇于尝试和挑战的革新精神值得学习。影片开头说过,这是我做过的一个梦。因而无论是小孩还是青年,他们或多或少具有黑泽明本人的影子。无论是对战争的厌恶,对艺术的追求,对人类的反思,对环保的呼吁还是对死亡的看法,这些都是萦绕在黑泽明大脑,伴随他度过一生的问题。人生如梦,这一个又一个的梦,不但关于人生,还关于或丑恶或崇高的人性。
第一个梦:小朋友在一个阳雨天里头不听妈妈的告诫,偷窥了狐狸的婚礼,触怒了狐狸。狐狸留下一把匕首给妈妈,让她转交给小孩并要求他以死谢罪。妈妈把小孩赶出家门,叫他到狐狸的居所请求原谅。
第二个梦:女童节里,男孩在“第六个女孩”的引导下闯入桃园,与桃树的灵魂对话。桃魂要求他留在这桃园,为砍尽桃树的家人受罚。后来却发现男孩与家人不同,他是热爱桃花的。于是这些桃树的灵魂就为他带来最后一片怒放的桃花。
第三个梦:几个登山队员在赶往营地的途中遇上暴风雪,虽然营地就在附近,然而他们对自己、对队友的怀疑让他们在绝望中几乎全部毙命。就在最后一个队员弥留之际,他用坚强的意志力抵挡住了死神的诱惑,终于带领队员在阳光的指引下到达营地。
第四个梦:军官走过长长的隧道,在隧道的另一边看见死去的部下。
第五个梦:年轻人走进梵高画的世界内,拜访凡高。
第六个梦:核电厂爆炸了,有毒的放射物质把万物赶绝,把大地变成一片废墟。一个科学家、一个青年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被逼到海边,科学家跳崖,剩下青年妇女在做无力的反抗。
第七个梦:在一片死寂的废墟里,青年遇到了“食人魔”。得知这个世界受到辐射的影响,已经畸形。人类变成食人魔,弱肉强食并被头上生出的角折磨着。
第八个梦:青年来到一片世外桃源。这里的人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平静安稳。青年见证了这里的一场“快乐的葬礼”。
电影的多个段落都采用舞台化的造型和环境。短短的十几分钟内,虽然只有寥寥几人的对话活动,但人物的身份安排本来就具有代表性。巨大的矛盾与冲突被浓缩在零散的小故事当中,种种元素造成的张力表达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深刻的意旨。
第一个梦里,小男孩对狐狸的窥探行为是一种人类猎奇本能驱动下的僭越。男孩代表人类的阵营而狐狸所捍卫的是自然界的秩序。母亲的角色充当公正的裁判。男孩的探险发生在丛林,茂密的树丛、斑驳的阳光和晶莹的雨水把大自然的清爽透亮表现了出来。也为狐狸的出现提供一个神秘并充满灵气的舞台。在景别方面采用大全景。构图方面,近景是壮实高大的树木,密林中行走的小孩仅占很小的比例。男孩的稚嫩弱小和大自然的伟岸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白雾中若隐若现的神塔和传统戏剧的配乐“仙化”了丛林(日本传统戏剧大多起源于祭祀活动,表达一种对神灵的敬畏),为狐狸的出现进一步营造气氛。雾中的狐狸造型不但舞台化,还很有日本传统戏剧的特色,从造型到舞步都规整考究,在刻画狐狸“神灵”身份的同时强化了“秩序”这一概念。同时也影射了躲在大树后的小孩对秩序的破坏。破坏秩序的小孩受到的第一重惩罚是失去了“家”,紧闭的家门隔离了他与过往单纯宁静的生活。第二重惩罚是“以死谢罪”。故事的最后是男孩拿着匕首,在一片山花灿漫中走向彩虹(狐狸的居所)。在这里,彩虹的作用只是再一度神化狐狸这一大自然的“神灵”,并不代表狐狸已经原谅了小孩。遍地的鲜花与前方灰暗的山景形成色调上的强烈对比,预示一个并不明朗的未来。人类应该负起责任来,为自己鲁莽的行为赎罪。
第二个梦里,随着小男孩的移动,一树桃花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桃红的柔光。周围暗沉的色调和门框都对桃花起到了强调作用,使她显得特别的圣洁,特别的美。随后小男孩进入房间,鲜红的布匹以明亮强烈的色调引起了小男孩和观众的注意(当然小男孩注意它的目的同样是引起观众注意)。陈列在红布上的女童节人偶精致华丽。它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今天是女童节(日本的女童节人偶平时都是收藏起来的)。几个人偶的镜头越切越近,灯光把它们打得晶莹剔透,神情栩栩如生,仿佛要活过来一般,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给桃园里的“桃魂”一个静物的参照,以至于观众看到后来的“桃魂”时就会想起它们并产生对照。在男孩观看人偶的过程中,传统戏剧的配乐响起。它与随后“桃魂”起舞的那一段音乐相同。影片借助这两方面的讯息暗示观众,男孩在桃园里看到的“桃魂”实际上就是女童节的人偶。在日本,女童节人偶是有灵魂的神圣祭祀物。而影片在这里把人偶和桃树的灵魂画上了等号,一方面增添童话色彩,一方面把桃树神化,同时也把没有感情的树木人格化。于是自然生态的代表“桃魂”与人类的代表男孩开始了冲突两方的对话。对话过程中,男孩在地势上处于最低处,所以镜头经常要采用俯拍,而“桃魂”的地位显然是高高在上的。他们(尤其是王)拥有裁定的权力。他们声音空灵、服饰高贵,代表着自然一方的神圣力量。然而被他们所质问的小男孩显然没有丧失热爱自然的本性。“桃子可以用钱买,但是要上哪儿去买一片开满桃花的果园呢?”孩子问“桃魂”。这时采用的是“桃魂”的主观镜头,通过这样一个换位,孩子面对着镜头向观众、向人类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一场桃花瓣的雨下得满满的,那一枝枝怒放的桃花占满了整个屏幕。紧接着一个个突兀的桃树干把男孩的美梦打碎,也用强烈的视觉反差震碎观众的心。到这里,动人的旋律陡然降了八调,周围一片静默。怅然的音乐响起,男孩四顾,独剩一树桃花在风中摇曳。
第一个梦和第二个梦同样运用了日本传统的戏剧风格来体现大自然的神秘神圣。所不同的是,第一个梦关于惩罚,第二个梦关于奖赏。第一个梦体现的是自然神秘严酷的一面,而第二个梦却是它亲和美丽的一面。所以在音乐上,第一个梦相对诡异阴森,第二个梦却有一种祭祀或盛会的味道。从服饰上来说,狐狸的服装采用冷色调(即使是婚礼),而“桃魂”的服饰采用的是暖色调。两个梦都是关于孩子的,它表现的是一个小朋友的梦。因此无论是布景、光色还是剧情设计都充满了朦胧奇幻的味道。
一片风的怒吼声把观众带入第三个梦。画面灰蓝,能见度很低,几个登山队员步履蹒跚走在一片冰雪覆盖的世界里。呼吸声、脚步声和其他动作的声音都被不同程度地放大。后景发生雪崩,前景尖而长的冰从上方垂下,厚厚的雪一直积到人的大腿。而人的身上也铺着一层白雪。整整六分钟内没有一句对白。画面和音效都在单调中强调着这恶劣的处境。这样的开场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种疲惫、严寒、险恶和艰辛。观众在感觉上度过的时间不会仅有六分钟。登山队员同样感觉到时间的延长效果。意识模糊的队员说出第一句台词:“天又黑了。”这无疑更添绝望。在绝望中,队员们开始怀疑:怀疑方向,怀疑时间,并且失去了坚持的毅力。只有走在最前方的那一位,他坚持时间没错,方向没错。“我们的营地就在不远的地方。”他是最清醒的一位,也说明他是意志力最坚强的一位。这为他随后摆脱死神诱惑提供个性基础。一个又一个队友倒下了。死神伪装成温柔的美人,对他进行催眠:“雪是温的,冰是烫的。”让人舒心的安魂曲飘荡,队员在轻抚中几乎睡去。而睡去意味着死亡。当他用最后的意志企图起身时,突然一阵暴风雪的斯吼打破了宁静的歌声。在声效上,现实与幻象产生对比,体现队员在意识上的自我斗争。虽然神情依然温婉,死神按在队员脖子上的手却近似于掐喉。她头发在风中飞舞,在队员的反抗中,她终于恢复了狰狞的面目,随风飞走。这是一个关于意志力的梦。抵抗的级别逐渐升高。首先是恶劣的环境。这是可以看见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大家都调动起浑身的意志力对它进行抵抗。但诱惑是无形的,那美丽的面孔,那温柔的微笑都与死神的概念相去甚远。所以队友们说完“有人来”就倒下了。诱惑是对意志力的最大考验。甚至会有观众看完故事还不知道那位美人的真实身份,甚至有人即使知道那是死神的诱惑都选择安详地睡去。这就是诱惑的恐怖。大师所描绘的诱惑不但考验了登山队员也考验了观影的人们。既然迷幻让人沉醉,又有多少人愿意选择清醒?然而赶走死神之后,暴风骤停,画面变得清晰,阳光再次出现,美丽的风光只留给坚持到最后的人。队员在胜利的号声中举目四顾,看见巍峨的群峰被冰雪覆盖,雪花在峰顶飞舞。很明显,这些空镜头要么调用资料要么外出取景,然后利用蒙太奇的链接效果使他们产生关联,使得成功的喜悦通过一片美景在摄影棚中被放大。当然,摄影棚内的色调光线都要小心配合这些美景。美景神情交替切换,渲染成功的欣喜。营地被太阳照得发亮,夸张地设置在几步之遥。意图表达“紧要关头不放弃,绝望就会变成希望”。
第四个梦,男人的服装表明他军人的身份。镜头跟随着军人,背景从一派自然风光转向幽深隧道。军人主观镜头,黑色的隧道越来越近。黑色代表死亡、悲哀和压抑,而隧道隐含着对时空、生死的跨越。军人走向阴阳的交界。一只恶狗从隧道跑出,对着军人狂吠。腥红的灯光打在它身上,使它看上去更加狰狞恐怖,仿佛是从地狱闯出来的恶灵。长长的幽暗隧道,与回音重叠的脚步声,制造出一种恐怖、阴森的气氛,让人不安。当军人走出隧道时,象征死亡的夜幕已然降临。隧道中走出了一位牺牲的战士。战士的造型非常舞台化:暗红的血迹深深地渗透在破烂的军装里,皮肤泛白透着蓝灰色,脸部通过夸张的化妆效果描绘出骷髅头的模样。那是一副恐怖的死人的造型。就这样,战争中的惨死者和生还者被放到了一个画框内进行对话。战士的第一句话就很自然地交代了主角的身份:“指挥官。我真的殉职了吗?”对生存的愿望,对家人的眷恋使得这位士兵不能相信自己已然惨死。一步步的进逼,一个个的疑问,指挥官哑口无言只能一步步后退,被逼到墙边。画面中士兵处于左上角而军官处于右下角,两个极端的位置配合两个极端的身份,张力拉得很大。战士指着远处群山当中的一点灯光,转过头来,悲伤地说:“爸爸和妈妈还在等我回家。”这个画面相当漂亮。远处的群山在夜色中都已灰暗,只有山中那一点白光色调如此明亮,为战士的归途指明方向。但再明亮它也终究是一点而已,那么伶仃,那么微弱。就像一捏就灭的希望。近处战士在遥望,远处亲人在等待,但他们已经阴阳相隔,永远走不近彼此。这就是画面的感染力,也是大师级的功力。如果镜头只是对着战士,哪怕再大的特写,再凄凉的表情都不足以表现这一种绝望。这样的绝望是战争带来的。它夺取的不但是生命,还有希望、和平与爱。无伦是死是生,都得饱受它的折磨。第三小队整齐站在隧道口,队长报告:“无人伤亡。”根据之前的观影经验,观众可以从造型上辨别,他们其实已经全体阵亡。视觉与听觉造成的极端反差造成生与死,荣誉与屈辱的强烈对比。指挥官的自责以及对战争的恐怖回忆被形象化为一只狗,从隧道的入口尾随到出口,从生尾随到死。战争的可怕回忆将会伴随着他度过一生。那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创伤。在这个故事里,通过死生者的对话,黑泽明把战争的罪恶狠狠地披露。那是在利益与征服欲的诱惑下,显露人类劣根性的愚蠢行为。
告别了风雪肆虐,告别了死亡隧道,镜头展现油彩描绘的凡高。青年入镜。镜头跟随着他展示一幅幅凡高的作品。青年拿起行囊,戴上帽子,走入凡高画的世界里。镜头通过这些动作隐喻:是凡高让这位青年走向油画的世界,走向创作的世界。随着西方古典旋律响起,凡高名作《吊桥上的马车》在洗衣声和谈话声中活起来了。青年向画中的洗衣妇人问路,洗衣妇人语带讥讽:“小心,他住过疯人院。”一句轻描淡写的嘲笑道出了凡高的困窘:就连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不朽形象也笑他是个疯子。可见当时的他与世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凡高的画作没有对基督的颂赞,没有对圣经故事的复现,没有对贵族的谄媚,他终其一生在歌颂太阳歌颂自然。他的画作没有达芬奇与伦勃朗的细致逼真,他表现的是彭湃的激情、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光明的向往。黑泽明早年热衷于绘画,成为画家可能是他终生未能实现的梦。但他有着和凡高一样的艺术激情与执着。他们同样尝到过不被世人理解的辛酸。“黑泽明之于电影,的确就像他自己塑造的武士一样,有殉道者的执著,甚至带点儿疯狂的意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和斯皮尔伯格,和科波拉,也和伊斯特伍德不同。在好莱坞的这些大人物看来,电影最多只是一种生命中的价值,而对黑泽明来说,电影就是生命本身。黑泽明曾经躲在卫生间里割腕自杀,原因就在于不能拍电影导致精神崩溃。”黑泽明说:“我,减去电影,等于零。”这种疯狂与执着籍由他眼中的凡高反映出来。一身染满油彩的凡高看见青年手拿画板,第一句话就是:“Why aren’t you painting?”——你不需要站在后面战战兢兢对我顶礼膜拜,如果你热爱画画,你必须拿起笔来。而你该崇拜的不是我,而是伟大的自然。大师利用一组隐喻蒙太奇把凡高作画的镜头和火车行驶的镜头交互切换,表现出他那种作画的激情和冲劲。黑泽明特别选择凡高失去耳朵之后去“拜访”他。针对世人对他切耳行为的疑惑,电影里的凡高解释说:“我画不好自己的耳朵,所以把它们切了。” 且勿论这是否凡高切耳的本意,但这就是黑泽明眼中的凡高。于他而言,“凡高,减去绘画,等于零。”他在借凡高表达着自己以及自己终生追求的境界,当然也顺带借凡高赞颂美丽的自然风光。凡高走后,青年在火车的鸣笛声中奔跑了起来。之前的一组蒙太奇把火车与凡高的创作激情相捆绑,所以在这里,本不该出现在麦田里的鸣笛声变成了一个符号,它标志着凡高精神对青年的鞭策。随后青年籍由特效带领观众行走在凡高的画作里,黑白的景物映衬出一个硕大的红太阳。那是凡高的标志。画作按照青年的身高比例被放大,甚至观众可以看到坑坑洼洼的油彩。利用这种特效,黑泽明给观众一个机会,通过凡高的画作,深入、细致地去感受他的内心世界。故事以凡高最后的名作《麦田里的乌鸦》收尾,从虚幻回到现实,与开头呼应。那些乌鸦代表艺术家孤苦寂寥的内心深渊,黑泽明有意夸大乌鸦数目,他所宣泄的是同样的悲怆。与开头青年戴上帽子的动作呼应,青年凝视《麦田里的乌鸦》,脱下了帽子。他代表黑泽明本人,向凡高致以崇高的敬礼。
色调从清晰明朗转向模糊灰暗,第六个梦的开头一片恐慌。雄伟的富士山在一片火海中仿佛震怒的天神。人类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山下四串逃命。逆流行走的主角被突出。大师非凡的构图再次产生隐喻和对比:富士山所代表的自然阵营与人类之间力量悬殊。在美丽的富士山被激怒后,日本变成炼狱,渺小的人类无力反抗,只能逃命。悬崖边满地垃圾一片废墟。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开始充当“说书人”的角色,告诉观众发生什么事。本来没有颜色的各种毒素不但被“染上”了颜色,还如同瘴气般飘浮在空气中。影片通过这种手法把威胁形象化,使得冲突更加明显。也很直白地表明,这片土地人类无法再踏足。一番对话引出穿西装者的身份——“对不起,我就是那些罪该万死的人之一。”这句话一道出,几个人即刻归类到了不同的阵营里,他们不再是单纯的逃难者。男人、妇女和儿童,这三类受害者一类比一类无辜,一类比一类脆弱。他们和肇事者站在一起,一方疯狂地质问诟骂,一方愧疚地看着惨状听着怨愤。肇事者身着西装,分明暴露核工业给他带来的利益与地位。然而妇女却牵着两个未懂事的孩童,背着一个婴儿。一方面刻画出她伟大的母性,从而与残忍的灭绝摧残产生对比,一方面强调他们的可怜无辜。一个大爆炸把中年男人充满悔恨愧疚的脸照亮,然后他跳下悬崖。在享有金钱与地位之后,懊悔与灭亡尾随而来,这就是肇事者的结局。辐射扩散到悬崖边,男子在红烟的包围中拼命抵抗。生存的渴望变成男子拼死的挣扎,在布满屏幕的红烟之中显得无力。象征灭绝的红烟愈加稠密,让人绝望,让人窒息。这一个梦表达了黑泽明先生对核问题的忧虑。
一片死灰的大地,阳光透过密布的浓云投向一片废墟。青年行走了近四分钟,跨过山头,走过瘴雾,还是一片灰的死寂。与第四个梦的开头异曲同工,黑泽明有意把这些简单的画面讯息反复交代了四分钟之久,旨在观影感受上传递给观众一种没有生命痕迹的荒芜。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影出现在雾中,在造型、环境和姿势的强调下显得诡异狰狞。他头上的白角虽小,却由于它本身颜色的高调突兀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在日本,这是食人魔的造型。因而在日本人看来,这个造型会更加恐怖也更有寓意:人类的自大自私把自己变成了吞食自己的怪物。另外,在环境塑造上,就连美的代名词——花朵,也变成了这副模样。以畸形的植物衬托畸形的人,人类僭越本分破坏自然和谐,造就了这么一个不堪入目的世界与自己。人类被辐射成食人魔的模样,过着人吃人的生活。即使在文化灭绝,濒临绝种的关头,阶级依然存在:角多者欺压吞食角少者。在这里,食人魔不但是说书人和引导者,更对人类破坏生存环境的愚行进行犀利指责。腥红的水塘边,许多“食人魔”痛苦地嘶叫。这地狱的景象在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告诉世人,破坏生态这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什么景象。起到很好的告诫作用。这个梦一方面是再度以辐射和环保为题材,另一方面也把人类最丑恶的灵魂暴露。
在述说了七个梦境以后,大师用来结尾的第八个梦,有关于死亡礼赞。同时也把他的理想国展现在世人面前。那里没有锋利的匕首,没有突兀的树桩,没有肆虐的风雪,没有狂吠的恶狗,没有爆炸的核电站,没有死寂的荒芜。美丽的大自然展现在观众面前,穿越过浓烟与废墟之后,画面里水车转动,流水潺潺,一切安宁祥和。平淡的乡间景色忽然显得如此珍贵。这样的景致无疑与第七个梦的结尾处产生极大的对比。一天一地的生存状态使得观众很直观地做出本能的选择趋向。在青年与老者的对话中,老者语调平淡却句句指向人类的愚昧。通过他俩的问答,“水车村”的观念与现代社会的观念产生对比碰撞。老者说出的正是黑泽明本人的心声:一种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生存法则。在说话过程中不断穿插美丽的风光和青年的表情,在镜头语言上增加老者言语的说服力。故事开始时,一群孩童排着队伍,采花放到一个块石头上。无论是小孩的行动还是青年的视线都将焦点引向那块石头。石头的地势较高,摆放在画框的中心位置,青年离开后,镜头为它停留好一阵。这些强调都使观众产生好奇,对它留下印象。后来利用这个伏笔,故事很自然地引入死亡礼赞的主题。原来那是一个浪人的坟墓。浪人一生漂泊,孤苦无依,客死他乡。然而水车村里的人们却给他一个美好的归属。死亡于他而言反而变成了一种解脱,一个安乐的归属。这时画外传来若隐若现的庆典乐声,通过老者的一番解说,很自然地把死亡庆典渐渐带入。“年纪大了,自然就会死的。” 人生在世做出贡献,死后理应得到尊敬。这是达观,是顺应自然。阳光透过树荫投下斑驳的光影,村民抬着遗体一路载歌载舞。在经历了七个故事的坎坷征途后,那是一个安详的歇息,是一个句点,是极乐。也是黑泽明所向往的最终归属。
这部影片具有很强的实验性质。在两个小时的观影时间内,黑泽明向观众展示内容上毫无关联的八个小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主题都很深刻。在短短的十来分钟里如何把主题突显,起到预期的教化作用,这个问题很考功力。大师极力调动起环境、造型、动作、构图和声效等电影技巧,让它们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叙事。人物极具代表性,台词不但一针见血,还不时会有大段的说教,甚至会代表黑泽明本人,直白露骨地把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这对传统艺术(尤其在中国)所讲求的留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画面上,有说黑泽明与主流创作者不同,追求的反而是平面化的构图。在电影里,有些背景的构图已经表现化到与舞台背景靠拢的地步(在第6、7个梦里尤为明显)。到底这样的效果好是不好就见仁见智,但是大师在80岁高龄还勇于尝试和挑战的革新精神值得学习。影片开头说过,这是我做过的一个梦。因而无论是小孩还是青年,他们或多或少具有黑泽明本人的影子。无论是对战争的厌恶,对艺术的追求,对人类的反思,对环保的呼吁还是对死亡的看法,这些都是萦绕在黑泽明大脑,伴随他度过一生的问题。人生如梦,这一个又一个的梦,不但关于人生,还关于或丑恶或崇高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