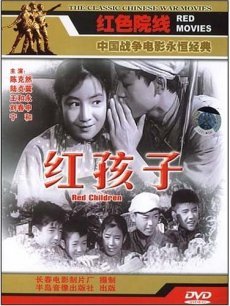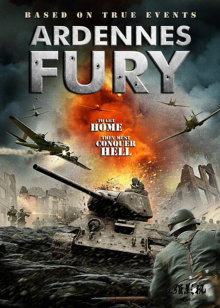- 西瓜云2
- 西瓜云1
- 西瓜云3
- HD
- HD国语
- 正片

紫蝴蝶
- 主演:
- 章子怡,刘烨,冯远征,仲村亨,李冰冰
- 备注:
- HD国语
- 类型:
- 战争片 剧情,爱情,历史,战争
- 导演:
- 娄烨
- 年代:
- 2003
- 地区:
- 大陆/法国
- 语言:
- 国语
- 更新:
- 2024-03-14 11:58
- 简介:
- 1928年,伪满洲国的日本翻译伊丹英彦(仲村亨)离开中国情人丁慧(章子怡)返回日本,数年后他再回中国来到上海时,变身高级特务。而这时丁慧已变成地下抗日组织的成员,并与该组织首领谢明(冯远征)相爱。抗日组织去火车站接从外地聘请的暗杀日本情报人员山本的杀手时,误认其为小职.....详细
1928年,伪满洲国的日本翻译伊丹英彦(仲村亨)离开中国情人丁慧(章子怡)返回日本,数年后他再回中国来到上海时,变身高级特务。而这时丁慧已变成地下抗日组织的成员,并与该组织首领谢明(冯远征)相爱。抗日组织去火车站接从外地聘请的暗杀日本情报人员山本的杀手时,误认其为小职员司徒(刘烨),混乱中,丁慧杀死司徒女友依玲(李冰冰),司徒则被伊丹英彦抓获。对一系列遭遇无比迷惑的司徒被释放后,发誓要为依玲报仇。丁慧与伊丹英彦重逢,变成两股势力互相设局要利用的重要棋子,她本人正为误杀无辜饱受内心折磨。某个日本会所举办的舞会上,伊丹英彦告诉丁慧山本与谢明均已死,丁慧震惊想刺杀伊丹英彦之际,司徒持枪闯进舞会。
——边缘之于中心的动荡与暧昧。 影片《紫蝴蝶》是对于电影叙述边界探索的一次先锋性成果。先锋意味着独创,是未经验证的新鲜试水。最后的成果难免会有旁逸斜出之处,但最值得品鉴的也是其自由之声句对习见场景的破译,它带来了依循另一模式的思维,以及具有连带关系的艺术表达法,即使进步中也存在混乱和杂糅的成分。这也是第六代导演总体面临的时空转场中语言壅塞与排堵的必然挑战。 抛弃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第六代导演与先锋派文学同根同源,又与后现代表现手法脉理暗通,电影与文学现状影射了社会场域更迭带来的普遍性遭遇。在经济世界愈演愈烈的脱节与反叛之下,强大文化中心的长期聚吸同时也会滋生出一种倾向抽空与再造的离心力,指向另一种宣叙的机锋。具有群体归纳性的独特风格化标志由此形成。 张旭东评价贾樟柯电影风格时说:“这是一种对现实进行认知测绘的尝试,它们刻画了中国碎片化社会空间内部的特殊拓扑学。”碎片呈现并不意味着完整的缺失,而是达到了更真实层面上的概括性。第六代导演试图用日常性代替戏剧性,用开放性代替封闭性,从而消解行为的目的性和终极意义。它对电影内部和谐的传统逻辑做了一次打破和重设,对统一、集中和主流话语的权威进行了彻底的逆向背离。一种强烈的边缘性由此产生。 电影《紫蝴蝶》是第六代导演娄烨的代表作。仔细观摩娄烨以往的作品,无论是《苏州河》、《颐和园》还是《紫蝴蝶》,皆带有明显的仿自然主义痕迹,同时又有着蒙太奇学说对于象征镜头的组接和拼贴技巧,这两者分别是写实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表现和再现的一种平衡。在《紫蝴蝶》中,景别设置多为近景和特写,消除了审美距离,与被表现人物呼吸相闻,情感互通,提供了一个深入审视人物内心变动的角度。即使是烧杀抢掠的大场面,依旧使用近景镜头描画,制造出一种冲撞感和同步性。镜头与人的视线持平,将人物放在同等尊重的立场上交流,表达了摄影机背后的创作者力求以正常姿态介入完整立体的“人”的潜在坚持。长时间追逐人物背影的跟镜头,依赖主体运动来控制构图,也是冷静旁观的叙述方式的展现。对自然声的大规模收取,更是生活还原的写照。 然而导演并未让自身意志完全脱离电影叙述把控,相反,导演并不忌讳运用形式感强烈的象形镜头来勾勒思维路径,以传达对影像的主观性塑造。如同繁复巴洛克式的结构和叠化、重复、跳接的手法,都无一例外地传递出导演对故事内核的独特理解,增添了影片的思想外延和意识创造。 贝尔托鲁奇说:“人是历史的人质。”在大时代洪流的裹挟中,人们面对命运无常徒劳无功。作为片名出现的中心意象,是一只玻璃瓶里的紫蝴蝶,美丽而脆弱。它挣扎着用翅膀拍打空气来证明自己存在,但改变不了瓶外的世界。所以,在无力的现实面前,导演选择去除个体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人”的潜在压迫,剥离历史传奇的负累,将焦点锁定在人物身上,用富有实效的特写镜头呈现生命的真实状态,捕捉到每个人面部最细小的抽搐,以及内心趋近毁灭的折磨。此种觉察类似欧洲电影感性精神和深度挖掘的美学作风。 影片开场的持续性沉默,构筑了一种失语的困境,包含了“小我”的情感基因在历史大环境下的无处安放,人物如同处在历史与政治夹缝的真空之中。辛夏与伊丹街头步行回家,在家中相视无言,再到辛夏火车站送别伊丹,都上演在减弱色彩的如同曝光过度的滤光镜中。画面清冷单薄,人物缄口不语,个体层面的情感沟通仿佛被淹没到了压倒性的强烈干扰的环境杂音之下,丧失生命温度与活气。 故事非线性剪辑的跳跃和零乱暗示着个体命运偶然关联的叙述基础,原本毫不相干的几位主角聚集在同一时空,因误会和意外走向一种错综的联结。这是战争背景下的普遍性命题。人物处于“被卷入的状态”,事态和人物发展一起失控。最典型如司徒的命运,因错穿接头人大衣而被误认,紧接着陷入一场完全与之无关的党派纷争。又如同丁慧(辛夏)与伊丹的上海重逢,有着相当成分的偶然性。因其因果关系的丧失,对追根溯源的失败必然导引向故事层面的彻底混乱,理性变得毫无意义可言。这种对世界存在秩序的解读破除了商业电影中惯常运用的叙事密码,使电影更接近于复杂心境的卷轴式展现而并非情节设计的吸引眼球。 在室内场景中,画面黯淡晦涩,人物形象多为低调光下的剪影,有如堕烟雾之感。极度静谧的空间氛围构成另一种性质的重量悬置在空气中,狭小的活动范围中弥漫着隐隐的威胁。反复出现的点烟镜头,是人物内心起伏挣扎的侧写,是历史迫压下人性的短暂喘息。当场景转向室外,画面通常由躁动不安四处飞奔的人群、枪炮轰鸣带来的鲜血和熊熊燃烧的火光占据。人群与火光是导演的一组常用象征,人群寓意着强势的盲目与胁迫,火光则是久久压抑下的混乱爆发,如同大潮中无力无助的人们内心的呼号。大段手提摄影和虚焦镜头带来的煽动性与融入感,又是一种极致的动荡,与先前的虚静形成强烈反差。独立个人角落始终要被迫进入时代整体的震颤之中,人物被放逐于喧嚣的世界荒原之上,无处可逃。 影片通过正侧面刻画充分展现了人在历史大环境中的符号化过程,具有强烈的隐喻和透视意味。镜头内游动的人脸无一例外都是忧郁深重的,他们无法掌控自身命运,正如橱窗里展示的木头玩偶一样。报社人员的面目模糊无从辨认,司徒女友伊玲做接线员的繁忙工作场景的反复再现,代表了历史洪流中一粒微尘的机械运转,逐渐沦为无名无姓的同质化机器,宏大符号质押下的末端零件。长镜头的铺设使人产生一种耽溺的昏睡感,这也正是随时代巨浪翻滚的人物出于适应环境需要自动抽离情绪,走向麻木漠然的心理映射。 丁慧(辛夏)与谢明作为该层面上的一组对比关系存在,暗衬了人性在泯灭边缘上的挣扎往复。谢明是斗争中的理性主义者,他性格中的残酷与冷峻是摧残情感寄托后达到的一种极端。司徒无意间知道行动的秘密后,他毫不犹豫地打算开枪杀了他,但遭到丁慧阻拦。谢明说:“他是个祸害,像他那样的人多了。”他的情感发泄也是生硬的,动物性的,如同他与丁慧的性爱,在一种生僵的、冷漠的但狂烈的方式中进行。 而丁慧则是情感与理智的捆绑体。她有两个名字,正代表着她身体中的两种力量属性,包含了两种自我认证,存在分裂与撕扯的潜能。“辛夏”是美丽梦幻的异邦名字,生长在伊丹所描绘的与世无争的文学社里,是逃离历史与政治之外的本原身份,是空虚的精神代称。而“丁慧”则是她在政治斗争中的符号,具有现实的功能性,简单直接却又意蕴含混。在这一重自我里,她试图抛弃作为人的情感,用纯粹的理性来支配行动。但她终究无法斩断情感掣肘,最终因此丧命。在与旧情人伊丹的几次相处中,她都泄露出了软弱的本质。民族与个人的情感矛盾令她惊恐而徘徊,这是对原有秩序的摇晃与怀疑。无比反叛,也无比真实。 在最后的舞会场景中,伊丹拥着丁慧跳着舞。伊丹贴着她的脸说:“我们的计划成功了。”丁慧的眼睛猛地睁大,渐渐溢满泪水,恐惧被放大到窒息的程度。惊讶、慌张、痛苦、绝望种种情绪在她扭曲抽动的脸上依次轮转着。她缓慢地后退,惶惑而惊恐。镜头转向伊丹,他正在用满是鲜血的手颤抖着点烟。 导演说:“其实这部影片就是一棵树,看到辛夏跳舞结束时,这棵树就死了,此后的一段是死亡的树枝,它透露出这棵树活着时的信息。”这棵树的死亡,也寓意着时代巨音下独立个体的呻吟彻底被掩埋。 在《紫蝴蝶》的末尾,导演出乎意料地回到故事起点,使故事结构更加完整,意旨更为确定。在火车站事件之前,丁慧与谢明刚刚经历了一场绝望而暴虐的性交。出发前的这段对话,在阴郁和潮湿的氛围中,人影晃动不止,揭开了藏匿于故事浮动之中的核心主题,为影片的完结又添了一层迷离与狂乱。 丁慧: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谢明:没有。我很好。 一阵沉默。 丁慧:谢明,你跟我认识一年多了,对吗?你还记得上次在一起什么样吗? 谢明:去年夏天,你也是在那儿跟我说,谢明,我们这样不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我们可以在一起战斗。 丁慧:你同意了。 谢明:是,我同意了。你呢?一年了,你觉得怎么样? 丁慧:挺好的。 谢明:真的? 丁慧:真的。至少我们都活着。 谢明:至少你还活着,我们还在一起战斗。 丁慧: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一阵沉默。 谢明:我们该走了,要不就晚了。 丁慧: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我这些天一直想哭。 丁慧抬起头,迷茫、困惑又似略有清醒地问了一句:“我们为什么要战斗?”把冲锋中被遗忘的人性逼向了最深渊,也是最核心所在。它瞬间推翻了一切乔张作致的既定意义,抛给我们一个根本性的疑问。然而,以人物微薄的力量无法作出回应。当二人准备停当坐入车内,叮当作响的电车正载着前去火车站接司徒的伊玲驶过。人物命运演绎着奇妙的错过与相遇。谢明问丁慧:“准备好了吗?”镜头缓慢地摇到陷于黑暗中模棱难辨的丁慧的脸。她停了几秒,看似下定决心地轻轻说:“准备好了。”进入战斗状态的人们,已然忘记了曾有的情感挣扎。 不知自己该去往何方的人物并未因此停下脚步,这其实是一种无从选择的困境。他们依旧沿着来时路一步步走向那个厄运的结局,警惕而盲目。导演没有留下一丝夹缝中的希望聊以自慰。但如斯宾诺莎所说,希望和失望都不应是善。不存在的虚妄希望,终止了失望如疾病般的蔓延。 导演以处在时代颠簸边缘的人作为叙述对象,但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地位提升到了视像中心。其方式在于,影片展现的所有“历史的”、“政治的”或者“客观的”外部环境,都不过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外延。它们会以何种面貌出现,无一不以契合主人公内心情感为原则。强大的心理外化手段使原有的视觉素材烙上了远超其本身的含义印记,使影片获得某种方向的升腾。最后出现的长达三分钟的抗战影像资料,充满了毁灭、死亡、崩塌与残暴,原本只是客观的历史记录,以意识形态的角度还可以解读出某些普遍的政治意味。但因放在特殊的位置,又配上了旧上海风情舞曲的音乐,一种巨大的不协调感由此生发,但也因此带来了富有建设性的意义重塑。它完美地成为了女主角内心扭曲、撕裂与痛苦的视觉化描述,镜头与画面竟变得如此不可单立的统一,甚至使得这段影像作为历史资料的原本面貌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也正是导演对强势话语的一次反讽形式的突围,体现了导演自觉摒弃民族与个人神话,挣脱历史文化的挟裹,将人从重重符号中释放出来,裸露生命真实状态的追求。这反映出导演对于重心安置的主张:即使是大写加粗的符号,依然无法掩盖个体生命的真实状态。导演试图把握某些共同情感,从而建构起一种纯粹的艺术,使之更贴近生命本源。 《紫蝴蝶》试图拨开符号遮掩的重重迷雾,创立一种崭新而脱俗的语境。对抗战、革命等传统话题进行隐讳的反向思索,是一种对根系的窥探与抚摸,对异时空中人性的打捞与复原,通过电影语法使思想蕴藉获得了一种自由成像的可能性。影片的局外人视点也是一种逆向的回归,这也正是边缘之于中心的相对性——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剖析曾在大时代集体围攻下沦为边缘上的呓语,但当电影与文学的边缘化叙事逐渐趋向普遍时,新时代版图中的边缘与中心的倒置随即显现。 “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党,却有着合法的姓名和身份。”《紫蝴蝶》中的这句话暗示了新一代导演在大众眼中亦正亦邪的隐秘性与公开化。但当这些为主流话语所不容的导演们以代际身份被重新命名时,我们发现他们仍然被收容到了具有聚合性的体制之内。因广泛存在的流变性,“边缘”的定标模糊不清,边缘与中心的界限,也会处在永久的动荡与暧昧当中。